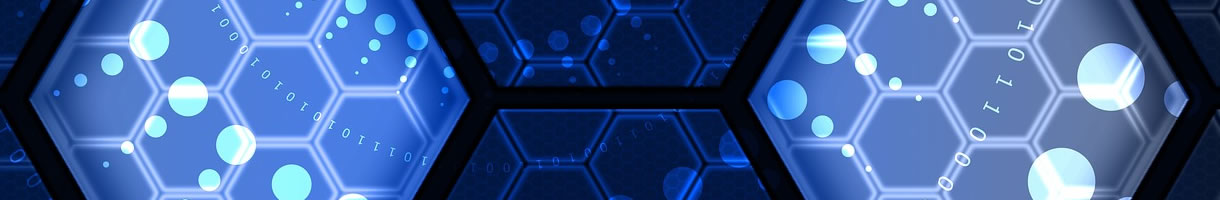花神魂归净土孕万芳, 火神折翼堕幽川赎罪: 宁宁, 来世莫再遇我
声明:本篇内容为虚构故事,如有雷同纯属巧合。
我是四界里独一份的六瓣霜花,十年前嫁作火神夫人。
直到我咽气第十年,他才想起踏足花界寻我——只为取我真身炼化,救他那命悬一线的白月光禾禾。
我的闺蜜告诉他,花神已死,万花枯萎。
可他满脸不耐,放出九天玄火炙烤花界。
“不就没了个孩子吗?这般不识大体。”
“赶紧交出六瓣真身,她还能做个贱妾。”

1
花界穹顶忽然炸开大片赤霞,火红色的凤凰振翅撞开护界结界,尖鸣着坠落在百花潭边。
花界早从六界仙班中淡出,堂堂火神肯屈尊踏足这荒芜地界,断不会是来接我回去的。
鸣阳凤目里翻涌着不耐烦,一声沉喝便将火神威压铺天盖地压下来。
“花宁呢?滚出来见我!当年教你的尊卑规矩都喂了花灵虫?”
迎上他的只有小蛮——我当年的闺蜜,如今花界仅剩的活物。
小蛮正蹲在花冢前,默不作声给每株枯花浇灵泉,那些枝干都是我们当年一起养的伴生花。
“花宁死了十年了,火神殿的消息这般滞后?”
鸣阳皱着眉闭了闭眼,指节捏得咔嗒响,勉强压下窜起来的火气。
“那丫头最是贪生,怎么会轻易咽气?”
“不就是没保住个魔胎?当年巫医明说那胎带魔息留不得,她闹着要和我和离,闹到现在还没闹够?”
“莫不是听说禾禾被魔器所伤,故意藏起来躲着不肯救?”
鸣阳指尖泛起赤色灵力,顺着花冢里每株枯花的茎脉探进去——他总觉得我在耍小性子,藏在某朵花里不肯出来见他。
许多刚冒出新芽的花枝,被灵力绞得断裂,连有些枯败的枝桠都被连根掀翻,小花们疼得蜷起了柔弱的枝条。
可无论他如何动作,小蛮都只是机械地重复那一句。
宁宁已经不在了,连魂魄都散了,你放过她好不好?
鸣阳直接挥掌扇在她脸上,小蛮颊边立刻浮起一道血痕。
这世上只有我的九天玄火能伤她,我从未对她用过,她怎么会死?
呵——可若这世上会九天玄火的,从来都不止他一个呢?
我以火神殿下的名义命令花界,立刻交出罪人花宁,否则休怪本尊不留情面。
小蛮愤恨地盯着他。
宁宁在你心里,就只是个罪人?她已经没了,是非曲直,我不想多说。
鸣阳瞬间恼羞成怒,见小蛮仍不肯透漏我的下落,扯出一声冷笑。
禾禾要是醒不过来,我要整个花界给她陪葬。
他直接命人绞断了所有草木的根系。
还不说是那个贱人藏在哪?
小蛮不可置信地坐在地上,望着一地残败的花枝断桠。
当初你重伤垂死,是我花界所有人拼着灵气救的你!
许是想起从前那段不堪的过往刺痛了他。
鸣阳气急反笑,阴鸷的目光扫过四周,眼底翻涌着狠厉。
贱人,我知道你没断气——你跟她情同手足。
三日后你若仍不现身,我就把她丢进神兵营,让我手下的人好好“疼”她。
你总不愿见她沦为千人骑的玩物吧?
话音未落鸣阳便拂袖而去,小蛮再也撑不住,哇地吐出一口血,软倒在地上。
鸣阳为逼我现身,竟拿小蛮作饵——我们相伴千年,她是我在这世间仅剩的牵挂啊。
可我早就死了,死在他那白月光的九天玄火里。
小蛮艰难地往前爬,爬回我的闺房,看见墙上的画像,才安心地合上眼。
我喉咙像塞了团浸了水的棉絮,哽咽得发不出声。
“傻小蛮,疼不疼啊?”
她挨了一记九天玄火,灵根定然被烧得剧痛,可她像没知觉似的,蜷在角落,脸上是小心翼翼的满足。
“宁宁,别怕,护不住你,我就来陪你。”
我们从前约好,要一起守着花界,踏遍万里河山。
可我却食言了。
2
鸣阳根本没耐心理等三日,第二日便又来了。
想来是怕白禾多受半分苦,要生生炼化我——若是我自毁霜瓣入药,药效反倒差了些。
哪怕我要受千刀万剐的罪,他也半分不会在意。
见小蛮身边连个鬼影都没有,他眼里的嘲讽都要溢出来了。
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?花宁为了自己那点心思,说走就走抛下了整个花界。
你要是把她的下落说出来,我保你坐上花神的位置怎么样?至于她,禾禾已经答应让她留下做个低贱的妾室。
他本以为小蛮会对他千恩万谢,哪成想小蛮居然对着他脸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,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句话。
花宁当年是祖神亲赐给你的正妻,你居然为了个贱人要置她于死地!你对得住祖神的嘱托吗!
鸣阳何曾受过这种侮辱,再加上被祖神的名头压着,立刻火冒三丈挥出一掌。
小蛮连滚了不知道多少圈才停住,看那样子五脏六腑怕是都被震得碎了。
我扯着嗓子喊让鸣阳滚出去,抓着他的衣袖拼命扯,可压根伤不到他半分。
我和禾禾打小一起长大,是她心眼小容不下人。
她以为躲起来就能万事大吉?要是耽误了禾禾的病,整个花界都得跟着完蛋。
白禾见他提到祖神,怕鸣阳动摇,立刻靠进他怀里。
殿下,凡事都是命里注定的,或许禾禾本来就该有这一死。
哼,既然本来就该死那就去死啊,又反过来打我的真身的主意干什么?
听见白禾抽抽搭搭的哭声,刚才还有些犹豫的鸣阳眼神更坚定了。
要是找不到她,我就把花界每一株花灵都炼化了,看她能躲到什么时候。
3
白禾指尖缠着鸣阳腰侧的玉带绕圈,发顶蹭着他小臂,眼尾泛着淡粉,眼波里浸着软乎乎的春意。
小蛮指甲掐进掌心,眼眶红得要滴血,吼得嗓子都哑了。
“宁姐姐才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!你们这对狗男女!”
“你们居然要拿宁姐姐的命换这个狐精!宁姐姐要是没了,她也配活?”
鸣阳眉峰一拧,抬了抬下巴,旁边神卫立刻狞笑着扑向小蛮,拽她的领口。
小蛮挣扎着踢翻一个侍卫,可架不住人多,很快被扯得只剩月白里衣,目光像淬了毒的刀,戳在对面两人身上。
鸣阳被那目光扎得眉心一跳,沉着脸转过脸去。
我看着侍卫的脏手在小蛮身上乱摸,恨得胸腔都要炸开。
鸣阳,你当年说过要替我守着娘家人的,这就是你的守?
白禾却忽然勾了勾唇,唇形动了动,没出声。
“这只是开始。”
她明明已经亲手把我刺得半死,却还不肯罢休,非要看着我咽气才安心。
十年前我好不容易怀上鸣阳的孩子,她却买通巫医说那是魔胎,会克得她魂飞魄散——转天她就开始吐血,连着三天昏迷不醒。
鸣阳盯着我,眼神里全是犹豫,我哭着喊。
“这是我们的亲骨肉!两族混血的血脉多金贵,怎么会是魔胎?”
“要是真的克她,我立刻回花界养胎,再也不碍她的眼!”
白禾倚在窗沿,眼尾挂着泪,轻飘飘看了鸣阳一眼。
“殿下,要以大局为先——姐姐回花界的话,祖神又要责罚你了,不如……让我走?”
不过片刻,鸣阳便下了决心,让人按住我灌下堕灵汤。
“不过是个见不得光的孽种,怎配和禾禾比轻重。”
我被锁在房里足足哀嚎了三日三夜,一盆盆血水往外端,到第四日才堕下那个已经成型的男胎。
我拼着最后一口气求她,想再看孩子一眼,她却附在我耳边,声音轻得像蛇信子:
“那孽种啊,早被剁碎了喂殿外的狗。”
我急火攻心扇了她一耳光,鸣阳却以为我要伤她,挥掌碎了我的心脉,将我关在暗室里“反省”。
白禾派了下人们轮流来折辱我,更在没人时用凤族的九天玄火,烧得我灵根都烂了。
我浑身皮肉都烧得翻卷开来,拼着最后一丝灵力从天宫逃回落花界,是小蛮扑过来接住了我。
她望着我奄奄一息的模样,慌得手都在抖,只能抹着眼泪拽着我往天宫赶:
“宁宁,别睡——我带你回天界,找祖神要公道,他肯定能救你!”
路上被鸣阳的人围追堵截,她浑身是血,却还是拖着我跪到了火神殿外。
可殿里正张灯结彩——鸣阳要给白禾办一场六界皆知的大典,昭告所有人,白禾是他放在心尖上的人。
别为那种狼心狗肺的货色再来扰我。
那日白禾受六界叩拜时,我的灵根正被业火焚断,最后咽气在小蛮怀里。
我抚过自己瘪下去的小腹,孩子没了也好,免得跟着我这没用的娘受委屈。
只是鸣阳,你当真这般恨我?恨到我都魂飞魄散了,还要把我榨干抹净?
白禾脸上渐渐泛起诡异的潮红——那是她旧疾发作的征兆。
鸣阳开始发疯似的找我,咬定我就藏在这满院花枝里。
小蛮冷眼看着他,直到他祭出一支凤翎。
凤翎就这么轻飘飘落到他掌心。
他眼里先掠过一丝慌乱,紧接着脸就白成了纸。
4
我们也曾蜜里调油,山盟海誓过——情浓时他亲手把凤翎插在我发间。
“我的赤翎就这一支,宁宁,我的心意,你该明白的。”
我从前说过,凤翎绝不离身,如今我死了,它自然要回原主身边。
鸣阳紧攥着凤翎,我心头忽然浮起丝期待——期待他能想起我们的过往,想起我为他掉的那个孩子,别再难为阿蛮,难为花界。
可所有期待都被白禾细碎的抽泣声打碎,她红着眼眶,身子晃得像株要倒的柳。
“表哥竟把凤翎给了姐姐,终究是禾禾不配得。”
可姐姐怎能如此不珍惜,把凤翎说丢就丢,难道当真要和我们一刀两断?
鸣阳听了就要把凤翎塞给白禾,可这凤翎跟着我多年,早有了灵性,偏不肯顺从。
他急得红了眼,抬手就把凤翎烧了。
连主都敢忤逆的东西,留着有什么用!
我看着凤翎一寸寸化成飞灰,忽然觉得自己在这世上剩下的痕迹,也跟着一点点散了。
小蛮红着眼眶嘶吼着向白禾施法,可法术刚碰着她就被狠狠弹了回来。
白禾身上戴的护魂珠,分明是花界拼了全部力气给我的陪嫁,现在倒成了她的护身符。
鸣阳脸上顿时露出狠色。
别不识抬举,敢对禾禾无礼,我今天就替你主子教教你规矩!
不过是白禾受了点惊,他就紧张成这样,可我当年在天界受了委屈,他只会说我不懂顾全大局。
鸣阳的威胁像风一样刮过,小蛮压根没往心里去。
她每根毛孔里都渗着血,就算四肢被按住,还是拼了命要往前扑,眼睛像淬了毒似的盯着白禾,恨不能咬下她一块肉来。
鸣阳彻底气疯了,抬手就召出法相天地,我隐约猜到他要做什么,魂体忍不住发出尖锐的嚎叫。
他居然要撕开我花界的结界,把外面的恶灵放进来!
花界现在本就弱得撑不起,全靠这层结界护着,可结界一破,无数恶灵跟潮水似的涌进来。
它们贪婪地啃着每一株花灵的根骨,还有些刚化形的小娃娃,被它们拖到角落肆意糟蹋。
小蛮半张脸被啃得稀烂,森白的头骨都露了出来,一只眼球早被那大妖挖走。
我对着鸣阳不停磕头,我错了,我不该嫁你,不该拆你们的情分,更不该怀上你的孩子。
别再动手了,求你停手——我已经死了,已经给你们偿过罪了,别再伤小蛮啊。
可我做的一切全是白费力气。
我看着花界生灵遭难,半点办法都没有,眼里掉下来的不是泪,是带血的珠。
魂灵淌出血泪,定是受了滔天的冤屈。
5
白禾吸不到我的真身,身子一日比一日弱,连发间都冒了银丝——这是她强行用九天玄火的反噬。
可鸣阳只当她是天生体弱,反倒更疼惜她。
为了守着她,竟推了神军中所有事务,没日没夜地疼着宠着。
到最后竟对我下了四界追杀令,不管是死是活,只要把我的真身带回去。
霎时间三界生灵都动了起来,花界被翻得乱七八糟、满目狼藉,可我连半具尸身都没有。
被九天玄火焚死的花族,连三魂七魄都会化成飞灰。
他只以为我当年是受不住责罚才逃下天界,哪能想到堂堂火神正妃会死得这么惨。
鸣阳盛怒之下,每日都抓个花灵炼化了给白禾入药,花界被屠得生灵涂炭。
我披头散发像个恶鬼似的盯着他。
6
“鸣阳,你会遭报应的!”
“当年花界拼尽全力帮你上位,派了多少精兵才伤了根基,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!”
可鸣阳半点没入耳,满耳都是白禾的柔肠百转。
“表哥,禾禾能得你垂眸,已是几世修来的福分。”
“宁姐姐不肯救我,是禾禾命薄,只盼着山花漫山时,表哥能偶尔记起我。”
鸣阳听得心肝都揪成一团,怜惜地替她擦去眼角的泪,恨不能立刻取我入药。
可阴影里的白禾,嘴角却抿着抹得逞的笑。
她向来是两副面孔,当年我本想接纳她。
可她私下里却挑着眉对我说。
“你要是要点脸,就该自请下堂。”
“信不信我掉两滴眼泪,表哥就能毫不犹豫休了你?”
“我要是你早去死了——身为花神把花界折腾得快灭了,你也配活着?”
6
可眼下白禾惨白着脸倒在鸣阳怀里。
“殿下,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,就是没能成为你的妻子。”
鸣阳软着声音哄她。
“等你身子养好了,我就降神谕,迎你做正妃。”
“别哭了,嗯?跟只小花猫似的。”
白禾这才破涕为笑,用粉拳轻锤鸣阳的胸口。
“殿下惯会拿人家取笑。”
我正冷笑着看他们演这出戏,鸣阳突然朝我的方向扫过一道灵力
“何人在装神弄鬼。”
我心口猛地一跳,难不成我藏得不够严实?
却是白禾的侍女,攥着帕子在门口抖得像片枯叶。
“神君,找到花神了。”
鸣阳眼尾瞬间亮起来,抄起腰间法剑就带着八百神兵往那处赶。
我喉咙发涩——他倒真是把我当难缠的对手。
到了那处,只有小蛮孤零零跪在地上,对着枚泛着淡光的玉石花瓣叩首,鸣阳眉峰一挑,满眼都是嗤笑。
“别在这装腔作势,让她立刻出来。”
“她那样贪慕虚名的人,能舍得放下正妃的位子?”
我唇瓣动了动——原来在他眼里,我执着的从来只是个空名,那我攒了千年的心意,算什么?
小蛮抬眼看见他,声音冷得像浸了冰。
“你是来送宁宁走最后一步的?她半点不想见你。”
鸣阳鼻腔里发出声冷哼,指尖弹出窜九天玄火。
“让她赶紧滚出来,我没功夫陪你们演这出戏——再躲着,别怪我今日血洗这处。”
“你不是说她死了?那你手里攥着的,是什么?”
7
鸣阳指节一缩成爪,朝着小蛮面门劈过去,一把抢过那枚花瓣。
花瓣在他掌心里浮起来,像活了似的,泛着细碎的光。
小蛮捂着胸口的伤要扑过去抢,鸣阳却笑得更笃定。
“呵,她让你拿这个出来,是想让我念着从前的情分?”
这花瓣是当年他送我凤翎时,我回赠的定情物。
可白禾受伤那日,这信物被他狠命砸在我脸上,连带一声“毒妇”的骂名。
他掌心里窜起的火焰像吐着信子的毒蛇,缠裹着那片花瓣,可任凭他如何催动灵力,掌心的物件都纹丝不动。
他怒极反笑,指节发力捏碎了那块玉石,刹那间漫天扬起血色的霜花。
他怔怔望着天空,瞳孔里漫开一点慌乱。
须臾后伸手接住一片,指尖摩挲着霜花轮廓,嗤笑一声又摇头否认。
“这满空都是五瓣的,谁不清楚她的真身是六瓣霜花?”
“别想用这种把戏骗我——她肯定在这,我明明闻到了她的味道。”
他疯了似的催动九天玄火,要把我的踪迹烧出来。
可他微微发抖的手腕,泄露了心底的不平静。
透明的火焰像潮水般涌开,所过之处万物皆成灰烬。
我静静站在他身侧。
“鸣阳,别烧了——我真的,早就死了,别再造杀孽了。”
小蛮躺在地上,望着漫天坠落的血色霜花,笑出了眼泪。
“宁宁最是怕疼,当年被烧得皮肉都翻起来……”
“咽气前她就求一件事——再看你一眼。”
“我抱着她的残魂回去找你,想求你帮她聚魂,可你在做什么?你在给那个女人办封后大典!”
鸣阳像是想起了什么,脸色瞬间白成纸。
你根本不是想问她的下落。
小蛮目光钉在他掌心里。
鸣阳指尖摩挲着掌中的碎玉,像被火舌舔了一下。
她早不是完整的六瓣霜花了,只剩五瓣——你说她丢的那瓣去哪了?
8
人在情到深处时,总爱做些傻事,比如把自己的一瓣真身炼作定情的物件。
那时两个人如胶似漆,我满脑子都是小女儿的心思,既怕他看不出这份心意,又盼着他能懂。
如今再想这些,倒也没什么要紧了。
我望着鸣阳近乎疯魔般捧起玉石碎片,向小蛮发问。
她没死对吧?只是躲起来了对不对?
六界有的是灵丹妙药,未必非要她的真身——只要她肯给禾禾道个歉就行。
小蛮眼底浮着嘲讽,盯着他。
你不是要找小公主吗?你早就找到了——她就在你掌心里。
花界的生灵全在枯萎,今日漫天飘着血色霜花,你当真不明白缘由?
他怎么会感觉不到?只不过是不肯相信罢了。
是谁干的?到底是谁,能伤她到这种地步!
鸣阳终于撑不住,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。
他没了从前的高傲模样,只攥着那碎玉不肯松开。
小蛮字字带刺地质问他。
当年你中了毒,公主拼着名节给你解毒;你上花界求亲时,说要与她永不相负,可从来没提过你还有个青梅竹马。
祖神亲旨赐婚,你本有千万种理由推拒,偏生应得痛快。
成婚满百年,倒反咬我家公主善妒成性、容不得人,这世上竟有这般厚颜无耻之徒!
9
究竟是谁伤了她?她是我明媒正娶的正妃!
鸣阳吼得声嘶力竭,喉间的颤音藏不住心底的虚慌。
小蛮斜眼睨他,嘴角扯出抹讥诮的笑。
能引动九天玄火的血脉,除了火神一脉还有谁?你守着火神殿这么多年,会不清楚?
公主早伤了真身根基,为你拼着魂灯不稳怀了身孕,到最后连腹中孩儿都被人害了去。
你倒说说,她拿什么活?
你心里装的从来都是那个女人,趁早滚远点,别污了我们公主的坟茔。
小蛮是强烧着自身修为,才换得这几日能痛快说话的力气,说完便扶着墓碑大口喘着气。
鸣阳慌慌张张去拼那些玉片,指尖抖得厉害,碎片却像抓不住的光,怎么都合不拢。
不是的,我只是……只是……
只是后面的话,他自己也说不出口。
我是到死才想通——是他先移情别恋,偏要先给我安个错处,好让自己的薄情变得理所应当。
10
鸣阳蹲在地上捡那些碎玉,指尖被划得流血也不在意,起身时脚步踉跄得差点摔倒。
平日里连衣摆沾点灰都要换洗的人,如今袍子沾了满腿污泥,竟半分没察觉,模样狼狈得不像火神殿下。
他一路跌跌撞撞回火神殿,见着人就抓着问。
你们见过我家娘子吗?她怀着身孕,同我闹了点小脾气……
鸣阳哪里记得清我最后穿的衣物?只支支吾吾说不出完整的话。
才跨到门口,他忽然眼前发黑,直直倒在地上。
醒过来后整个人像换了魂,把自己锁在书房里,粒米不沾滴水不进,谁也猜不透他在忙什么。
白禾试探着推开书房门,随即眼睛一亮——她分明感觉到书桌上飘来熟悉的草木灵气。
她放下手里的食盘,踩着碎步喜滋滋凑到鸣阳身边。
“殿下,这是不是花神姐姐的真身?可、可怎么只有一瓣啊?”
话音刚落就捂着胸口咳了起来,发间几缕银丝顺着动作露了出来。
“哪怕只有一瓣也够了,禾禾从来不是贪心的人,就想多留在殿下身边几日……”
鸣阳冷冰冰瞥了她一眼,直接从她掌心里生生抠出那瓣花——白禾的手被划得满是血痕,他却连眼皮都没动一下。
小心把花瓣收进锦盒里,才转头对她说。
“这天下能治你病的灵药多得是,你为何偏要盯着花宁的真身?是谁给你出的主意?”
白禾像是被噎住了——她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,从前只要是她要的,鸣阳哪次不是顺着她?
怎么今日倒变了样子?
她揉着发红的眼眶,又提起那些翻来覆去说过的“委屈”。
“我本就福薄,母家又不如花宁姐姐的家世显赫,原以为只是和殿下年少相识的情分,哪成想竟碍了姐姐的眼……”
我这副身子骨实在不争气,倒不如死了干净。
她哭着,眼角余光不住往鸣阳身上扫。
鸣阳却捏着眉心,反将话头抛给她。
说你要用花宁真身炼药的巫医,可是当年指认她怀魔胎的那个?
他不是不怀疑,只是舍不得怀疑,如今竟要替我讨这迟来的公道?
可我和孩子都没了,要这公道又有什么用?
白禾脸上的笑扯得勉强。
殿下这是何意?我难道会拿性命编瞎话?
11
鸣阳还要再问,白禾忽然捂紧胸口昏了过去。
她原以为醒过来,又会像从前那样,要什么有什么,连我都得任她摆布。
从前她也总晕,只要一晕,我就得去赔罪。
我一个堂堂火神正妃,跪在她院门口,额头磕得血流不止,一遍一遍跟她念叨。
求白姑娘恕罪,是我占了你的位置。
她什么时候醒,我才能什么时候停。
可这次她打错了算盘,醒过来时屋里只有个侍卫。
殿下呢?他是不是去抓花宁了?
侍卫冷着脸回她。
殿下说,你醒了就打开桌上的盒子。
12
能有什么含义,不过是个轻微的警示,多可笑啊,我和孩子两条性命,他竟只舍得给白禾这么点教训。
他总认为白禾是受了歹人的蒙骗,可另一边又发了疯似的寻我。
六界上下,谁不知道火神的正妃不见了。
他去花界寻小蛮,卑微地仰起脸问她。
“宁宁,有没有话留给我,哪怕一句。”
可小蛮只冷淡地扫了他一眼,就让他瞬间崩了防线,他捂着脸,眼泪顺着指缝往下掉。
“算了,算了,她该是恨我的。”
我跟着他踏遍六界,他先在祖神殿外长跪不肯起。
可祖神早已经身归混沌,不然我也不会被糟践成这般模样。
他跪到膝盖露出森森白骨,也没等来半道神谕,只有三道天雷劈下来赶他走。
他又去幽冥河畔找我的魂魄,直挺挺地跳了进去,伸手摸索。
“宁宁,你在哪里啊,我来带你回家了。”
他的双手已经被河里的恶魂啃得鲜血淋漓,双腿也快废了。
幽冥主见他这副模样,只能无奈摇头。
早知今日悔不当初,花神早该去了四界之外的归墟!
念在你祖神当年的情分,我透你一句——她还有一魄没散,要是能寻回来,说不定……
鸣阳瞬间反应过来我就藏在那片玉石花瓣里,脚下生风般撞回火神殿,却撞进满眼刺目的画面——白禾正抱着那瓣真身啃噬,身上还套着我当年的正妃凤冠霞帔。
白禾捂着心口往后退了半步,声音发颤:“殿下,我听闻姐姐已经魂飞魄散了,那、那她剩下的真身碎片……”
鸣阳望着她,像是第一次看清眼前人似的,抬手就给了她一记耳光,力道重得让她撞在案几上。
“谁准你碰这瓣真身的?你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!”
白禾捂着脸抬头,眼里的泪珠子滚得更快:“分明是你之前说要把她的真身炼化了给我补魂的!”
见鸣阳哑口无言,她又软下声音,指尖拽住他的衣袖晃了晃:“殿下,往后我们总算是能安安生生长相守了……”
话音还没落地,鸣阳的手已经掐住她的脖子,把人抵在墙上,指节泛着青白。
“贱胚子,把你身上的衣服扒下来!你也配穿她的正妃服?永远都别想!”
白禾被他眼底的狠戾吓得浑身发抖,眼泪珠子滚着往下掉,手忙脚乱解开衣扣,把凤冠和霞帔都褪了下来。
临走前她还牵强扯出个笑,对着鸣阳深深福了一礼,踩着碎步退了出去。
到了更深露重时,她换了身月白素服,捏着帕子站在殿门口请罪。
“殿下,今日之事全是我昏了头,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……”
又是这副以退为进的样子,她用了百八十回,偏生鸣阳次次都吃这一套。
和从前每一次一样,他眼中浮着浓得化不开的痛意,伸手把白禾扶起来。
是我错了,不该把气撒在你身上——我们选个好日子成亲吧?
13
我倚在旁边的廊柱上,既觉得没滋味,又忍不住偷偷盼着什么——我早该看清这局面的,可就是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彻底离开。
两人的婚礼很快就提上了日程,白禾每天熬夜绣着红嫁衣,鸣阳却总一副提不起兴致的模样。
奇了,娶的是他心心念念的人,他怎么反而不高兴?
转眼到了婚礼那天,白禾披着层叠的嫁衣,正含着笑要拜天地,门口忽然进来个不请自来的人。
那人大步走进来——居然是“我”,眼神冷得像块冰,直勾勾盯着白禾。
席上的宾客全傻了——我的死讯早就在私下传得沸沸扬扬。
我也愣在原地——没人比我更清楚,我早就是个死人了。
那来的人又是谁?
白禾的脸瞬间煞白,勉强扯出个笑。
姐姐,这是回来喝我一杯茶的吗?快请坐。
鸣阳却突然冲过来,激动得浑身发抖,一把抱住“我”,还把白禾推到了旁边。
宁宁,是你回来了对不对?我们以后再也不分开,永生永世都在一起!
“我”却一声不吭,像个没有知觉的木偶,被他拉着坐在了主位上。
白禾身子晃了晃,端着茶颤巍巍朝“我”递过来,没成想茶盏摔在地上——她手上烫出一串红通通的水泡,还没等她露出委屈的神情,鸣阳就劈头盖脸骂了过去。
14
连这点最基本的规矩都摸不清,往后要怎么伺候我和花宁?
白禾眼眶红得快滴血,攥着茶盏哆哆嗦嗦跪下来,脑袋磕在地上赔罪。
我站在旁边瞧着这出乱哄哄的戏,心里直犯嘀咕该怎么收梢。
喜宴散了后,我跟着那具裹着我气息的身体进了正殿,到半夜时,忽然一道熟悉的赤光猛地往床榻上扑。
是九天玄火,摆明了要取床上人的性命。
可还没碰着床沿,就像撞进了层看不见的结界,跟水滴进大海似的,瞬间没了踪影。
鸣阳从偏殿里走出来,盯着面前的人开口。
“果然是你。”
白禾这才明白上了当——床上躺的根本是个傀儡人偶,身上嵌着那些碎片,也就沾了点我的气儿。
她一屁股瘫在地上,笑出声来眼泪却砸在裙摆上。
“对,就是我,你能怎样?”
鸣阳这些日子一直憋着劲查,除了他还有谁会用九天玄火,小蛮那天的话早就在他心里钉了根刺。
他皱着眉,声音里带着疼惜又带着恨地问白禾。
“你到底图什么?我都许了你平妻的位置,为什么非要赶尽杀绝花宁?”
白禾卸了那副柔柔弱弱的样子,眼神里的狠劲像淬了毒。
“图什么?你装什么糊涂?明明是我先跟你定的终身,可你先娶回家的却是她!”
“她能有祖神赐婚的谕旨绑着你,我就只能捞个空有虚名的封号!”
我立在侧畔垂着眸子,若是早知道她的存在,我压根不会嫁鸣阳。
白禾眼尾发红,偏执地盯着鸣阳。
反正她都死了,就当从没存在过,我们一家三口好好过不行吗?
她指尖轻轻抚过小腹,那里正笼着一层柔润的弧度。
鸣阳,你看看我啊。
话音未落就急切地去吻他的脸。
可鸣阳瞥见她的肚子,脸色瞬间煞白得吓人——许是想起了从前和我也曾有过孩子?
白禾樱唇动着,还在软声劝他,鸣阳却始终没半分回应。
说时迟那时快。
她早死了!你这么想见她,我送你去见!
白禾终于绷断了最后一根弦,趁他没防备重重劈了下去。
鸣阳脸白得像张纸,嘴里还在反反复复念我的名字。
白禾见他为了我这般模样,眼底红得要滴出血来。
你说过这辈子只爱我一个的,为什么还要记着她!
你的心里只许有我一个!
白禾这是彻底入了魔——以她的根骨本修不了九天玄火,除非堕入魔道。
眼看鸣阳最后一丝气儿要断了,我幽幽叹口气,飘向床上那具傀儡。
傀儡身上的僵硬感刺得我难受,可也只能忍着。
指尖凝出一缕极寒灵力,房中温度骤降,案上茶盏瞬间凝起冰棱,连空气里的水汽都结成细雪落下来,刚好裹住缠向鸣阳的那团赤焰魔气,将他从灼烧的痛苦里扯出来。
他踉跄着撑住桌沿站起来,伤口裂开的血浸透了中衣,不顾自己疼得发抖,反而哑着嗓子带哭腔喊。
是你吗宁宁?是不是你回来了?你出来好不好,就见我一面……
我知道错了,宁宁,我真的知道了……
15
花宁!你这个躲在阴沟里的贱人!滚出来!滚出来啊!
等我彻底掌控了这具傀儡木的躯体——关节不再发僵,指尖能凝出微弱的光影——才慢腾腾掀开内帐走出去。
鸣阳看见我时,眼睛瞬间红得要滴血,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,抬起的手悬在我肩前,又猛地缩回,像是怕碰碎了我。
我没心思看他,因为白禾盯着我的眼神像淬了毒的刀——她眼眶通红,指甲掐进掌心,血珠顺着指缝滴在地上。
这具木偶身本就不是她的对手,没拆几招她就破了我的防御,指尖带着黑紫色魔气直往我丹田捅——可鸣阳突然扑过来,替我挡住了这一下。
我愣了愣——他居然要护我?
不过是具木头做的壳子,碎了再雕就是,值得他用命挡吗?
活着的时候没得到的真心,死了难道还会稀罕?
鸣阳的手抚上我脸上的光影——那是用残留魂气凝的,碰一下就会散——他疼得直发抖,喉结滚动着却发不出声。
只能一个劲点头,嘴角溢着血,含糊不清地说。
宁宁……能再见到你……我死也值了……我一定会找到救你的办法……
可白禾看见鸣阳为我挡下那致命一击后,彻底疯了。
她腿间突然流出一股黑红血水——那是强行催动禁术的反噬——头发从发顶开始,一寸寸变成灰白,瞳孔里翻涌着滔天魔气,彻底堕入了魔道。
16
“你根本就不该活!十年前就该咽气的人,为什么要回来毁我和殿下的日子!”
她彻底疯了,指尖扣着我的手腕往墙上撞,指甲掐进肉里渗着血。
就在她抄起案上的金簪要扎我眼睛时,周遭突然静得可怕——风悬在半空,烛火凝着不动,连她脸上的狰狞都冻成了僵死的面具。
我终于落下回魂后的第一滴泪——那是小蛮带着全族拼了魂飞魄散的风险,发动时空秘术替我争来的一线生机。
我没再犹豫,掌心聚起魂族的青焰,直接拍在白禾的丹田上——她的修为像破了洞的布袋般漏光,疼得她蜷在地上抽搐,却连喊都喊不出来。
她被侍卫拖走前,突然从疯癫里醒了一瞬,爬着拽住鸣阳的衣摆,指甲掐进他的靴面。
“鸣阳,你说过要护我一世的!你不能看着他们带我走啊!”
可鸣阳连眼神都没分给她,他的目光黏在我身上,像溺水的人抓着最后一根浮木。
“宁宁,我们终于能长相厮守了。”
小蛮站在旁边,眼泪砸在青砖上,她拼命摇头,像是早知道我要做什么。
我冲她笑了笑,伸手抠下胸口木偶的心口碎片——那是我魂体的寄身,木屑飞溅间,木偶的四肢瞬间散成碎片。
熟悉的轻飘感涌上来,我又成了半透明的魂体,能看见鸣阳瞳孔里的我,像团要散的雾。
鸣阳发出一声断弦似的悲鸣,一头黑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白,肩膀塌得像被抽走了骨头。
我看着他崩溃的样子,轻声说:“鸣阳,其实我一直都在你身边。”
——你和白禾在我种的桃树下喂鱼,你下令烧了我族里的药田,你把我送你的玉镯敲碎给她做保胎药,所有你以为我看不见的事,我都看着呢。
他瞪大眼睛,踉跄着退了两步,后背撞在廊柱上,指尖抖得连袖子都攥不住。
他比谁都清楚,他的宁宁再也不会回头看他一眼,更不会原谅他那些荒唐事。
等处理完所有因他而起的乱子。
我的身子开始变得轻飘飘的,像被风裹着要往上浮,鸣阳瞳孔骤缩,连鞋都跑掉了,跌跌撞撞要扑过来抓我的手腕。
直到这时,压在我心口百年的执念才突然散了——原来我从来不是放不下他,是放不下那些被战火踏碎的花灵,放不下被他毁了的花界。
小蛮攥着我的衣角,眼泪砸在我手背,咬着嘴唇行花族最郑重的叩礼:“花神大人,求您让我过去,那是……那是我跟了三百年的少夫人啊,是大人唯一的正妃!”
我站在花界入口的金阳里,风裹着桃香钻进衣领,这是我几百年来第一次觉得心口不疼了。
远处鸣阳被仙兵拦着,嗓子都喊哑了,我盯着他发红的眼睛,只觉得像看一场没醒的梦。
我开口时声音很轻,风却把每一个字都送进他耳朵:“鸣阳,下辈子别再找我了,死生都不要见。”
话落时我身上开始飘起金粉,每一粒都带着花界的生机——我往花林走,脚边的枯草瞬间抽芽,折了枝的桃树重新开了满树花,那些被战火焚成灰的花灵,正从光里慢慢显出模样。
鸣阳终于挣开仙兵的束缚,扑过来时只抓住了我散在风里的金粉,指尖缝里漏下去的光,烫得他手背发红。
后来仙魔界都传,花神宁昭以魂为引,把自己的魂力拆成千万缕,全喂给了快枯死的花界。
火神鸣阳倒像疯了,亲手毁了自己的火灵根,散尽所有仙力跳进冥界,要受百鬼噬心之罚。
他的心被小鬼啃碎了又长,长了又啃,冥界的鬼差说,他是在赎当年毁了花界、伤了花神的罪。
只是每当老叟撑着渡船过幽冥河,他总扒着船舷问。
“宁宁,回来了吗?”
「全文完」